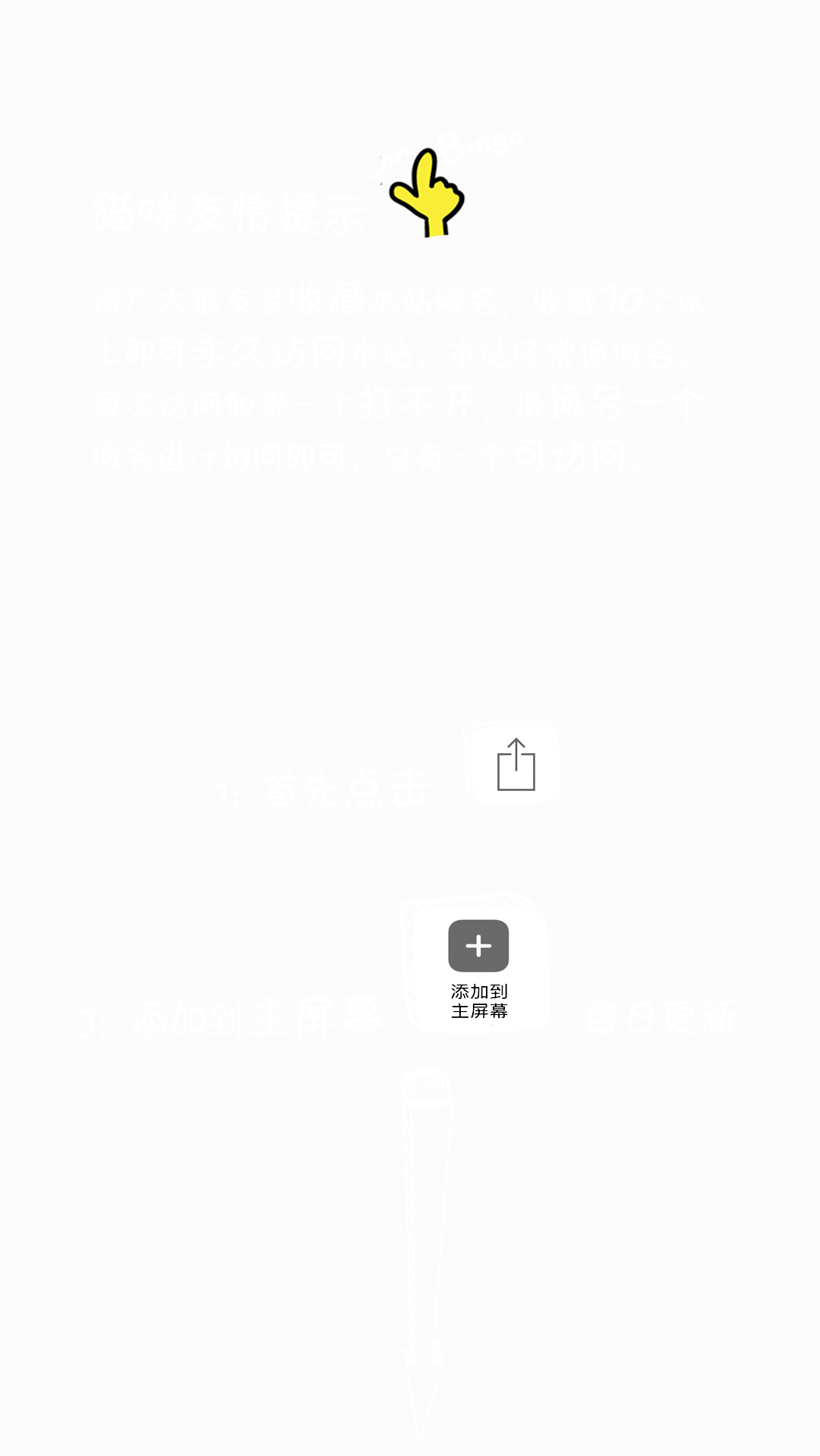略有点烫的水从花洒温柔的落下,淋在身上十分舒服,冲掉了沐浴露的泡沫,皮肤在沐浴露的滋润下显得特别光滑,当自己的手抚过乳房时,忍不住在已经有点发硬的乳头上多划了一圈,我禁不住发出一声呻吟。
我感到脸上有点发烧,也许是热水刺激的吧,毕竟已经很久没有过夫妻生活了。我克制住想要把莲蓬头和手伸向腿间的想法:“还是呆会儿让一郎来爱抚吧,那样的快感要舒服十倍百倍。”带着发烧的脸,我这样对自己说。
一郎已经洗漱完毕,上床去了。最近一郎不知为何情绪总是不太高,连以前很有规律的房事都有将近一个月没有履行了,有什么心事一直也不跟我讲。也许我该主动一点,大概一场温柔的性爱能让他重新振作起来也说不定。
我叫美蝶怜舞,今年25岁,丈夫小犬蠢一郎,结婚已经两年了。我们是大学同学,开学的第一天,一郎的姓氏就成为大家嘲笑的对象,每当我们起哄嘲笑他的时候,他都红着脸争辩说:“姓氏是先人传下来的,我又不能选择,再说我的名字和首相是一样的读法呢!”
大家就会接着嘲笑他:“你还想当首相呢?首相都是有钱有势力的家族做上去的,不知道你家是哪个世家大族啊?怎么没听说过呢,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这时候一郎就会红着脸,嘟起嘴巴不作声。那时候我只觉得他是个挺可笑的普通男生,并没有对他有特别的好感,只是觉得他这样被同学们嘲笑好可怜。 虽然有很多男生用各种方法追求我,但是我是来自秋田的——可以说是来自乡下的女生,一直以学习为重心,希求毕业时在东京能够找到一份合意的工作,在这里生存下去,所以并没有接受他们的追求。
大三的时候,学习的任务渐渐减轻,一郎开始追求我,多半是因为他纯真的眼神和被同学欺负时候的可怜可爱相在我心里留下的温情,大概也有一点点因为知道他是东京本地人士,我开始和一郎交往。
一郎有着理工科男生的诚恳和善良,也有一点点书生气的怯懦,他像宠女儿一样的宠着我,图书馆、食堂、教室、球场,处处留下甜蜜的回忆。
至于性方面,他当然也像其他的男生一样,都很猴急,可是我并不像同宿舍的其他几个姐妹一样,早早跟男朋友偷尝了禁果,而一郎也尊重我的意愿,要把第一次留到结婚以后。
我很辛苦的坚守底线,不仅与一郎也与我的欲望搏斗,奇迹般的守住了舌吻和最多让他在没人的地方揉捏我的咪咪这个底线,不记得有多少次他摸完我的咪咪自己跑进卫生间去打飞机解决,而他也不知道,每次他摸完我的咪咪,又不方便回宿舍的时候,我都得夹着湿透的内裤坐立不安好久。在日本这个性爱文化氾滥的土地上,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坚持,也许是来自秋田的影响吧。 大学毕业一年后,一郎在一家IT公司的工作稳定下来,我们结了婚,住在一郎的父母为他购置的一间小公寓里,而女性在IT行业找工作一向没有优势,加上一郎认为他的工资可以养活我们两个人,我加入了日本半数以上女性的队伍——家庭主妇,浪费了许多年学习的成果。
新婚的第一夜,一郎迫不及待的扒光我的衣服扑上来,我害羞的捂着脸,任凭他摆弄,虽然看了不少AV,他却还是找不到地方,在我下面胡乱的捅来捅去,他折腾了两分钟,突然软趴在我身上,等他从我身上翻下去的时候,我打开灯,坐起来看阴毛上点点洒落着乳白的精液,发出腥骚的味道,跟我的爱液混在一起,搞的阴毛湿答答的。
一郎不好意思的讪笑说:“大概是以前打手枪打多了,你也该帮我一下呀,你知道我是第一次,找不到入口的啊!”
“我也没有经验的嘛,人家好害羞!”
那天晚上虽然试了3次,我们还是没成功。婚后的一个月,我们都还是处男处女。
直到一个阳光明媚的周六,一郎和我一起去富士山玩耍,玩的很尽兴,两个人都累坏了,回家吃了饭澡都没洗就上床睡觉了。一郎从后面抱着我,很快沈入了梦乡。
周日早上7点,窗外小鸟叽叽喳喳的把我吵醒,我睁开眼,感觉屁股沟被一郎硬邦邦的小弟弟顶着,心里就起了顽皮恶作剧的想法。
我悄悄的爬起来,从厨房拿来打包用的透明胶带,轻手轻脚的把一郎的小弟弟缠起来,正当我缠到第二圈的时候,屁股上挨了重重一巴掌,我“哎哟”叫唤起来,坏笑的看着一郎。
一郎看样子也睡饱了觉,显得生龙活虎的,他一把抱起我,把我丢在软软的床垫上,又一把扯掉了小弟弟上的塑胶圈圈,“啪”一声丢在卧室的门上,朝我猛扑过来,嘴上还喊着:“坏孩子,看我怎么收拾你!”
一郎把我按在床上,把我已经分开的大腿抱在腋下,弟弟顶在我的下面,不知怎的,猛一用力,滋熘一声就插进了我因为玩他的小弟弟而略微有点湿润的洞穴里,我发出一声惨叫,用力抱紧一郎的身体,双腿死死的卡住他的屁股,指甲抠进一郎的嵴背。
一郎吓的赶紧停下来,心疼的问我:“宝贝儿,很疼吗?”
而此时他坚硬的肉棒插在我身体里,连根尽入,撕裂的疼痛和胀满的感觉让我说不出话来,只好使劲的点头。就这样僵持了半分钟,一郎求我:“宝贝儿,我好难受,能让我动动吗?”
我逐渐适应了疼痛的感觉,心想总不能一直这样吧,为了一郎的快乐,还是忍着吧。我把绞在一郎屁股上的腿松开来,一郎开始小心的前后抽动,棒身在撕裂的处女膜上刮来刮去,仍然很痛,但是蜜液却悄悄的流出来,缓解了摩擦带来的刺痛。
好在一郎坚持的时间也不长,3分钟后他就一泄如注,带着完成后的满足和疲劳感,我都没有感觉到精液从小穴中流出,就承载着一郎的重量进入睡眠。 做爱后的小睡可能也就十分钟,然而事后的换洗床单却花了我半天时间,一郎在我做家务的时间开心的出去买来我最爱吃的海鲜,打开红酒,点起温馨的蜡烛,庆祝我们的做爱成功纪念日。
第二次做爱是在我休养了一周之后,从那以后,我们开始了更加甜蜜的夫妻生活,虽然一郎总是三五分钟就交了枪,性爱生活差强人意,但日子就这样平淡而又幸福的继续着。
两个人计画着等一郎工作有所进展,有一点小积蓄的时候再要孩子,因此就采取着并不严格的危险期体外射精的避孕措施,也期待着万一中奖能够生个可爱的小宝宝,为一郎不在的时光增添一些乐趣。
然而幸福总是短暂的。一郎的母亲在我们大四那年因车祸去世,在我们婚后第一年的年末,一郎的父亲查出肛门癌晚期,为了给公公治疗,卖掉了公婆的大房子,经过半年抢救,虽然切掉了屁眼,老爷子还是没能保住老命,带着家里所有的积蓄,到那边跟老太太会合去了,留下我们小俩口,靠着一郎的工资收入,勉强过着小康的生活。从那以后,一郎的心情就一直不是很好,平淡幸福的生活蒙上一层淡淡的阴影。
我擦干身体,把浴巾围在胸部,吹干头发,轻手轻脚的进入卧室。紫罗兰色的床单上,一郎蜷着身体躲在薄被下面,初春的微风从窗外无声的吹过,偶尔传来树叶摇摆的声音,不知道什么花的芳香若有若无的偶尔飘进屋里,真的是美好的春夜。
也许是真的太久没有被一郎爱抚和操干了——我惊讶于自己脑海里跳出的“操干”这种粗话——我的乳房最近总有一种胀鼓鼓的感觉,乳头总是有一种想要向上翘的冲动,两腿之间也常常有一种湿热无法排解的气息在郁结。
我轻轻的钻进薄被,侧躺在一郎身边,将他的身体转向我,然后在一郎的耳边吹着气说:“一郎,睡着了吗?”
一郎说:“没有,在想事情。”
我腻着嗓子温柔而又坚决的说:“老公,别想了,我要!”
我拿起一郎的左手握住我的右乳,半硬的乳头碰到一郎粗糙的指头就引的我全身皮肤一阵发紧,我又拿起一郎的右手,放在我的两腿中间,夹着他的手轻轻的前后摩擦,小肉芽几乎立即挺立着从包裹它的花房间抬起头来,我都能够感觉到蜜液与意志无关的从小穴里流出来,流到大腿根部,痒嗖嗖凉嗖嗖的。
一向被动的我忍着羞耻,把因欲望和害羞烧红的脸颊贴在一郎的脖子上,下体在一郎的手上耸动着,示意他的手指能更进一步。
然而一郎却机械的动着手指,若即若离的在小肉芽上触碰着,却没有像以前一样把手掌盖在我的阴户上,也没有把中指插进我的阴道。我有点着急了,把手伸进一朗的内裤,却发现他的肉棒虽然前端已经流出了动情的口水,棒身却软软的没有起色。
我失望的对一郎说:“老公,你怎么了?要不我用嘴帮你吧?”
一郎愧疚的说:“抱歉,还是算了。”
我问一郎:“你最近怎么了?”
一郎嗫嚅着说:“没有,没什么了。”然后沉默了。
我只好追问他:“到底怎么了嘛?老公你有事情要跟我说啊,我是最爱你的老婆啊,这世上你只有我这一个最亲的人了,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呢?”
一郎又沉默了两分钟才说:“那个…其实我们公司要倒闭了…”
“啊!?怎么会?”
“很扯吧,日本IT业本来挺好的,没想到突然会这样,大概是国际经济大环境不好吧,加上海外来自印度、中国、台湾的竞争又很激烈,我们公司的猪头领导完全没战略眼光,所以才造成今天这样子吧。”一郎的声音里明显带着沮丧和不甘:“所以我就要丢工作了。”
“那怎么办啊?家里就靠你一个人啊!”
水电气、衣食住行、房产税等词汇一股脑的涌上来,我却只能忍着到嘴边的话。我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一郎明白这些事情的压力,所以一直瞒着我,何必说出来让他增添烦恼呢。
“只能去找工作了。反正还有存款,公司也能发一点遣散费,可以撑好一阵子的!应该没问题的。”我知道一郎这只是在安慰我,不然他也不会最近一直情绪低落,连做爱都没了兴致。
“这样啊…我也可以工作的。”
“没问题,可以的。”
一郎的同学大多数太太都是全职家庭主妇,他大学被嘲弄了几年,知道其中的辛酸和痛苦,所以不愿同学们再嘲笑他:“连老婆都养不起,没用鬼!”这样的话大概已经在他的头脑里转了很多圈吧。
“但是…”
“抱歉害你不安,快睡吧。”一郎转过身去,关了灯。
我本来很想把他的身体再转过来,却把伸出去一半的手又缩了回来。
“晚安。”
“撕蜜马三。你睡吧。”虽然一郎可能也睡不着,但为了不烦扰他,我起身帮一郎盖好薄被,离开卧室。
被这一事实打击的我全身都凉下来,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思前想后,为一郎的自尊心生闷气,也为自己的无能而懊恼,既然作为男士的一郎都丢了工作,我一个毕业就没找到工作的女人能怎么样呢?两年多的时间,专业知识也忘的差不多了,别的又能做什么体面而又收入高的工作呢?作为一个精力充沛的小少妇,总是这样逛逛超市、做做家务,不能为一郎分忧真是太没用了。
到底怎样才能帮到这个家呢?大概只能从朋友和同学的关系中去想办法了。 毕业以来,因为一直从事家庭主妇这一生职业,只认识几个同样是家庭主妇又有共同爱好的小圈子,几个闺蜜的老公、家人在IT行业也不具备能够提供帮助的资历,想从朋友当中找到出路是不太可能的了。那么同学呢?对了,去年冬天公公治屁眼癌期间,我一个人偷空去外面散心,偶然遇到大学时的好朋友梅蝶茶芜,曾经和她一起喝过咖啡,听她说起过老公三倍伊特翔在某知名世界500 强IT公司担任社长的职务,也许她能帮忙也说不定呢?
说起茶芜,可是个漂亮的女孩子,大学的时候虽然不住在同一个宿舍,但因为姓氏里都有一个蝶字,读音也很接近,爱好又比较一致,所以我和她的关系很好,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共同出入、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虽然她从来不提自己家里的事,但从她生活的品味上可以看的出来,茶芜的家境很好。
至于她的老公,想到他我不禁皱了皱眉头。茶芜的老公三倍伊特翔也是我们的同校同学,是工商管理专业大我们两届的学长,人长的很矮小,也很丑陋,那张脸一看就让人感觉不舒服,疙疙瘩瘩的像癞蛤蟆,但在学校社团的活动上却很活跃。
我们都很不解,为什么茶芜会接受伊特翔这样的人的追求,自从他们两个在一起之后,我和茶芜就渐渐疏远,想来去年冬天的偶遇是我们三年来比较亲密的接触了。
虽然有点不愿和伊特翔打交道,但是没办法,在这种时候又能怎么办呢,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只有他一个人算是有能力帮助一郎的了,而且又有茶芜的关系在,虽然很久疏于联系,如果可能的话,能帮还是会帮一下的吧。既然茶芜选择了他,想必他也有他不为人知的优点吧,我也不能太以貌取人了。
想好了这些,我马上拿出手机给茶芜打电话。一番寒暄过后,我吞吞吐吐的向她说明了给她打电话的意图,茶芜显得有点迟疑,在我的一连串的请求下,茶芜答应了我的请求。
挂掉电话几分钟后,茶芜的电话来了,说他老公愿意帮忙,但需要明天上班的时候当面详谈,并把伊特翔的号码留给了我。听到好消息的我很想马上去告诉一郎,但是转念一想,还是等明天见了伊特翔,有了眉目再告诉他吧,免得他空欢喜一场。
窗外的小鸟忽然又开始鸣叫起来,这么晚了,会是什幺小鸟还在叫呢?我走到窗边想看一看,树丛里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到。
昏黄的路灯下的暗影里,却有一对中学生,大概是刚参加完社团活动,在回家的路上,女生腻在男生的怀里,红黑格子的裙子一角撩起,白亮的大腿在夜色下闪着缎子一样的光泽。
虽然是已婚妇女,看到这种情况也禁不住羞红了脸,放下窗帘,心里咒骂一句:“小小年纪就这么不要脸!”